原标题:《反垄断法》的修订能打破“二分之一”吗?
“二分之一”已经成为国家市场管理组织的“关键”项目。
2015年发布了《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不得违反 《反垄断法》 、 《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限制、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是在线集中推广的组织者。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发行。在第22条中,由于电子商务运营商的技术优势、用户数量、控制相关行业的能力以及其他运营商在交易中对电子商务运营商的依赖程度,电子商务运营商显然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第三十五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操作人员收取不合理费用。
201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被修改,第12条正式将网上经营活动纳入监管范围,并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此后,虽然立法层面有所收紧,但司法运行层面几乎没有针对“二分之一”的司法判决。其根本原因如下:
首先,上述法律法规制定时,采用了粗而不细的一般原则,缺乏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细节。例如,在《电子商务法》中,从司法解释到专家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不一致和有争议。虽然第35条没有任何反对“不合理限制”的前提,但学术界的一些声音认为,行政力量将会增加,以干预市场,留下更多的运作空间, 《电子商务法》 尚具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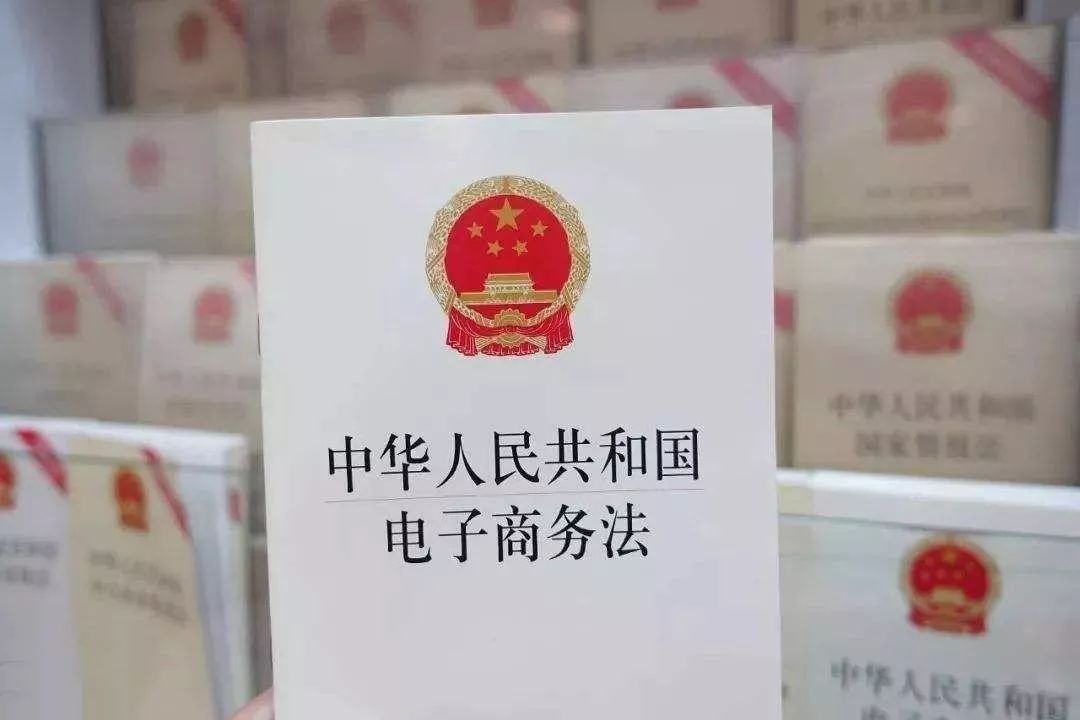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过程中,由于对“禁止滥用比较优势地位条款”的诸多争议,该条款未被纳入最终版本,这也给这一系列配套法律的司法运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第二,从国家角度来看,对竞争极为激烈的互联网抑或是新型经济业态的垄断或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要极为保守审慎,在那一年备受争议的“3Q战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明确的:腾讯在3Q大战中的做法(“二选一”及“捆绑QQ电脑管家升级”)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那以后,该行业几乎没有反垄断案件。即使在滴滴和优步的合并中,学术界在判断“市场份额”时仍然存在以下争议:1 .合并后的平台向用户收取的出租车费是否被视为市场份额的统计基础,或者平台扣除驾驶员佣金后的实际收入是否被实际用作判断“市场份额”的依据,这是有争议的;2.对于滴滴的行业来说,它是在线汽车市场,还是与出租车行业相同?
此外,58家与Ganji.com等互联网公司的合并也没有市场垄断的声音。
总之,虽然司法表面上在收紧,但由于缺乏落地性,使得以上法律对市场并未起到真正的“威慑”性,从2015-2019,“二分之一”将是今年11月的热门话题。如果没有意外,这仍然是明年的热门话题。
刚刚进入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持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征求公众意见稿),其中将互联网作为监管重点: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
第五十四条建议对违法行为采取极其严厉的处罚措施: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来不断提高监管能力。但是,在以前的立法中,对“二选一”的禁止性规定仅具有宣示性的意义,并没有独立的行为构成要件与处罚措施,这是市场出现诸多乱象的法律层面的原因。
那么,《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或者它能结束“二分之一”的问题?
《反垄断法》 :对互联网市场强监管进入实质阶段
在此之前的许多法律中,立法机关对“二分之一”做出了“定性判断”,也就是说,它不赞成商业伦理和伦理中的“二分之一”。然而,由于立法上的“漏洞”,行业进入司法层面的案例很少,法律的威慑作用没有发挥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学术界和立法机构对互联网产业,特别是基于平台的互联网企业的研究相对滞后。
例如,《反垄断法》传统上将“市场份额”和“行业进入门槛”视为垄断判断。然而,互联网行业的高市场份额并不意味着行业进入门槛高,高市场份额也不一定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在

阿里电子商务出现后,京东、品多甚至小红书都渴望尝试。尽管有许多尝试和错误,这个行业仍然处于完全竞争中。
如果我们
在《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在确定互联网运营商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时,还应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以及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这是互联网区别于传统产业的开始。在确定垄断行为时,市场份额和行业进入门槛不再是唯一的两个条件,而是加入了上述因素。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显然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行政自由。从解决纷杂的法律条文束缚,进入对互联网管理新的阶段,也是实质性的阶段。可以看出,在2019年底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会议”上,“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将是202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显然导致了两种观点。
支持者:
立法机关快刀斩乱麻,改变了立法落后于实践的被动现状,给管理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来加强市场监管,使“两个选择一个”远离市场。平台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对商家的胁迫和诱惑,SKU主导服务和价值,行业极其动荡。
反对者:
虽然互联网监管是单独列出的,但对于具体的标准和价值仍然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过度行政干预市场的可能性不仅会发生在执法过程中,而且由于表述不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还会回到传统行为的“市场份额”和“准入门槛”,这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在行业内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此前对垄断行为审慎的判定态度将成为过去式。
对于市场监管者来说,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将是下一步的关键任务之一。当有法律可循时,我们应该增加执法的灵活性。随着监管能力的提高和配套法律的完善,这对一些企业来说不是好消息。
其后若要落地,可在此基础之上同步修订 《电商法》 ,在此之前 《电商法》 起草团队也认为第三十五条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首先,我们需要对行业有利或有害的“二分之一”进行定性分析。

在最初的法律逻辑中,“相关市场的主导地位”中的“相关市场”的定义并没有详细说明。例如,学术界和法律界对于电子商务是否按照商业形态分类为零售,网上零售是否单独上市,或者平台电子商务是否被视为盈利性的“网上广告”,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是“二分之一”一直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如果我们从《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寻找灵感,并将互联网的“锁定效应”和“数据能力”维度作为标准,我们将看到以下行业现状。
近年来,虽然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仍然蓬勃发展,B2C电子商务平台模式却鲜有成功。在上述层面的支持与合作下,国内主要一线商家的资源大多集中在阿里、京东、苏宁等平台上,后两类大多是3C类。京东的服装和其他新兴品类也在“二分之一”的过程中死亡。尽管多多突然出现,但短期内仍采用“小B”(中小品牌或工厂品牌)扩张SKU的基本路线。一线商家的大多数旗舰店都集中在天马单一平台上。
在数据和锁定效应下,行业在短期内很难打破上述僵局而不解锁行政文件,这相当于提高了行业的进入门槛,降低了活力。
在这个水平,“二选一”能完全杜绝吗?
但是我们不认为在《反垄断法》之后会立即产生效果。
从行业竞争法的角度来看,创新仍然是电子商务行业的一个重要命题。2019年,电子商务行业有许多变量会朝着市场整体下滑的方向发展。“二选一”对B2C电商发展是存在一定阻碍作用的,也需要引起监管机构足够的重视。
当法律的具体规定不明确时,如果行政权力过大,上述平衡将被打破,市场将受到影响。因此,即使《反垄断法》修订草案能够通过,我们也建议主管部门采取谨慎的态度。
从操作空间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仍然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律,在以后的登陆中仍然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 《电商法》的同步配合。因此,配套法律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